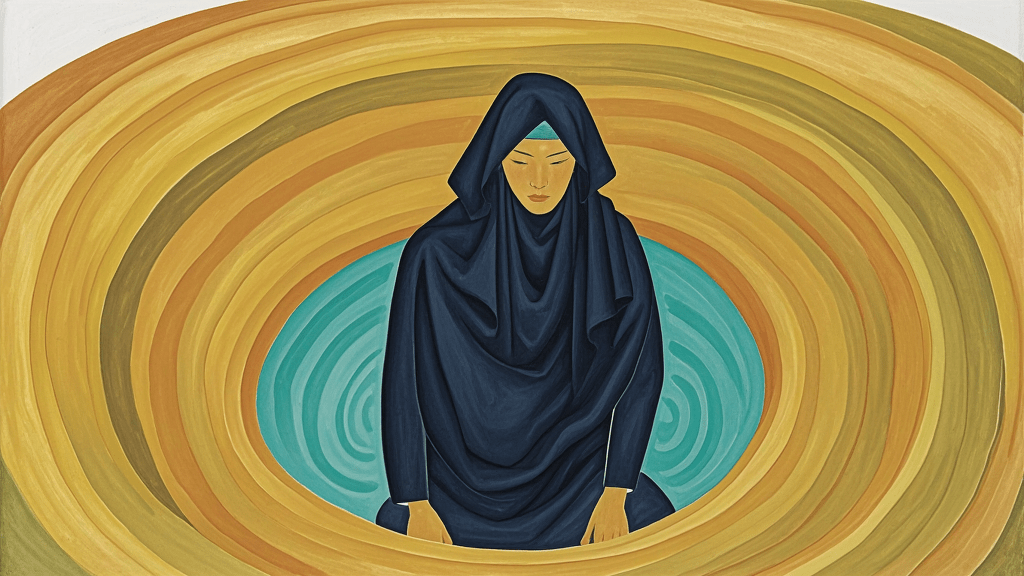
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《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们》在卡佛式的氛围中结束。读者很难联想到,这个短篇将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 70 万字(原文字数)长篇小说《奇鸟行状录》(赖明珠译为“发条鸟年代记”)的第一章。持久的铃声过后,是一场有关暴力的大梦。
啤酒喝到一半,电话铃响了。
“接呀!”我对着客厅的黑暗吼道。
“不嘛,你接嘛!”妻说。
“懒得动。”我说。
没人接,电话铃响个不停。铃声迟滞地搅拌着黑暗中飘浮的尘埃。此间我和妻都一言未发。我喝啤酒,妻无声地啜泣。我数至二十遍,便不再数了,任铃声响去。总不能永远数这玩艺儿。
感觉剥夺实验
“井”是这本小说中的重要意象。首先,二战期间间宫中尉在蒙古兵的强迫下跳井,经历过井下持续十几秒钟的阳光洗礼之后,他仿佛被巨大的力量摧毁了,“想不成什么更做不成什么,连自身的存在都感觉不出,仿佛成了干瘪的残骸或一个空壳。”在听过间宫的故事后,主人公冈田亨下到邻居凶宅的一口枯井中,静静思考妻子的失踪,并在其中通往一个类似梦境的世界。
小说中的“井”既是连接历史与现实,又是现实与梦境的通道,是村上春树这部小说的引擎,从现代的、无聊的世界,引向了历史中真实的暴力和梦境中虚幻的暴力。对于后者,相当典型的一例是,主人公在梦境世界中闭上眼睛把不知是谁打到断气之后,他的妻子又大声喊叫,“要是你想把我领回,就千万别看!”主人公在呕吐过后,身体回到了现实的井中,而此时枯井重新冒出水来。
村上这部小说的意象选取十分成功,我想,许多读者都会对井中的冥想充满向往。前面讲到,“井”是小说的引擎,务实一点说:感觉剥夺是幻觉之门。
你可以足不下井,在家完成类似的实验:在光线均匀的房间里,将一颗乒乓球刨成两半罩在眼睛上,并用胶带固定,确保看不见外在事物,只有光感。与此同时,戴耳机收听白噪音,并放松身体,静待花开。这种通过剥夺视听以产生幻觉的实验,就是所谓的“甘兹菲尔德实验”(The ganzfeld experiment)。这个过程不由得让人联想到“小黑屋”式的体罚,或是膜拜团体的精神改造——让你听到“内心的声音”,甚至就是最朴素的做梦。正如《走神的艺术与科学》中所写:“梦本来就是通过感觉剥夺锻造出来的幻觉,虽然它们与夜间眼球运动之间的关系表明它们是自然事件。”
在《诺门罕钢铁墓场》这篇游记中,村上记录下他所经历的一场幻象。深夜,村上在蒙古国宾馆的床上醒来,感受到强烈的地震,当他挪到房门前,按下电灯开关后,地震停止了,原来“摇晃的不是房间,不是世界,而是我本身”,这是对战争的恐惧所催生的幻觉。说到这里,我同样经历过夜间地震,床像是驶上铁轨,同车厢连接处一样横向摆动,旁边的书架几欲倾倒,怕是要拍在我身上,于是我十分愤慨,大喝:“非要这时候搬家吗!”
我上面发挥的这一段,地震是真的,大喝一声是假的,村上的游记或许也是类似手法。
除此之外,井底的视角本身带来了更多异象,比如间宫在井底的所见:
蒙古兵一起向井底的我撒尿。一直向上望去,他们站在圆形井口轮流撒尿的身影犹如剪影般小小地浮现出来,在我眼里恍若虚拟物,简直与吸毒产生的幻觉无异。然而那是现实。我位于井底,他们朝我洒射实实在在的尿液。全部洒完之后,一个用手电筒往我身上照。有笑声传来。旋即他们从井口消失了。他们走后,一切都陷入深深的沉默。
比如听到的井口风声:
时而有风声传来。风掠过地面时在井口发出奇妙的声音,仿佛遥远世界里女人的啜泣。那个遥远世界与这个世界之间有一细孔相通相连,因而啜泣声得以传来这里。但那声音的传来转瞬即逝,过后我还是独自留在深深的沉默与深深的黑暗中。
比如洒入井中的阳光:
我一动不动地待在井底,此外别无他能,甚至思考什么都无从谈起。我那时的绝望和孤独便是那样地深重。我什么也不做,什么也不想,一味静坐不动。但我在无意识之中期待着那道光束,那道一天之中仅有一瞬间笔直泻入井底、亮得眼前发黑的光束。从物理上说,阳光成直角射于地表是在太阳位于最高空的时候,因此应是正午时分。我一心盼望光的到来,因为此外无任何可期盼的东西。
那以后又过了很多时间。不觉之间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当我意识到什么猛然睁眼时,光已在那里了。我知道自己再次笼罩在压倒一切的光芒中。我几乎下意识地大大张开双手迎接这片阳光。它比第一次强烈得多,也比第一次持续时间长,至少感觉上是这样。阳光中我泪水涟涟而下,仿佛全身液体都化为泪水从眼中倾流一空,甚至觉得身体本身也融为液体就势流干流尽。在这辉煌的祝福中我想死又何妨。实际上我也想死去。此时此刻,似乎这里的一切都浑然融为一体,无可抗拒的一体感。是的,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仅仅持续十几秒的光照中。我应该在此就这样一死了之。
这一段心理与细节描写十分精彩,令人如入幻境,不禁忽略掉外蒙的纬度。此时的井,像是地球体内的一根刺,而井里的人已被遗忘在历史的缝隙之中。井中着实凶险,回想一下,本书诸多困境都发生在井下,而困境的破局全靠功能人(本田伍长、加纳克里他的幻影、肉桂)和超自然事件。
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睡眠
这不是专有名词,而是作家贾行家在播客“六进制”中提到的,当期标题为《让我夜不能寐的六个故事》。类似于目击者引发的连锁反应,故事中的凶手杀死了一楼和七楼两家的住户,或许是个冷知识,“杀人是相当累的”,在凶手的一刀一刀之下,他自己的生命力也在不断流失,等到杀死七楼的老太太之后,他甚至在楼梯间睡了一觉。这一觉就是所谓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睡眠”。
由于这个播客是会员才能听,我只是试听过两次,上面的复述大概与原文出入很大,原播客是在讲育儿经验也说不定,请读者留意。话说回来,陀氏能量巨大,大到能把尼采变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,影响了众多犯罪题材的文艺作品,估计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真的罪犯。
言归正传,我想谈的反倒是《奇鸟行状录》中最为“微不足道”的邪恶,或许也是最让人“夜不能寐”的邪恶——
笠原 May 这个女孩从短篇里出场时就是跛行,还戴着用来遮挡伤疤的墨镜,“弱小的肩头如机器的摇柄一般朝右侧有规则地摇晃”,据她所说,是“坐在摩托车后头甩下去摔的”。她没有说谎。等到村上的梦做到第二部,这里的摩托车事故才终于随着对死亡的讨论徐徐展开:
她衔支烟,一只手灵巧地擦燃火柴,戴上太阳镜。“你不怎么考虑死?”
“考虑当然也是考虑,但不经常。有时候。和世上一般人一样。”
“拧发条鸟,”笠原 May 说,“我是这么想的,人这东西肯定一生下来就在自己本体中心有着各自不同的东西,而那一个个不同的东西像能源一样从内里驱动每一个人,当然我也不例外。但我时常对自己不知所措。我很想把那东西在我体内随意一胀一缩摇撼自己时的感觉告诉别人,但没人理解。当然也有我表达方式不够好的问题。总之谁都不肯认真听我说下去,表面上在听,其实什么也没听进去。所以我时常烦躁得不行,也才胡来。”
“胡来?”
“如把自己闷在井底,骑摩托时两手从后面捂住开车男孩的眼睛。”说着,她把手按在眼旁的伤疤上。
“摩托车事故就是那时发生的?”我问。
笠原 May 露出诧异的神情看着我,问话好像没听到。但我口中说出的理应一字不漏传到她的耳里。她戴着深色太阳镜,看不清她眼神,但其整个面部倏然布满一种麻木的阴影,好比油洒在静静的水面倏然荡漾开来。
“那男孩怎么样了?”我问。
笠原 May 兀自叼着烟看我。准确说来,是看我的痣。“拧发条鸟,我非得回答你的问话不成?”
接着,她说:
“我害死了那个男孩。当然不是有意的。我只想逼到最后一步。以前那种事我们也做了好些次,做游戏似的。骑摩托时我从背后捂他的眼睛或搔痒似的捅一下肋部……但那以前什么也没发生,偏偏那时候……”
笠原 May 抬头看我。
“嗯,拧发条鸟,我没那么感到自己被玷污什么的。我只是总想接近那片烂泥,想把自己体内那片烂泥灵巧地引出来消灭干净。而为引它出来,我确实需要逼到最后一步,不那样就不可能把那东西很好地诳出来,必须给它好吃的诱饵。”说到这里,她缓缓摇下头。“我想我没被玷污,但也没有获救。眼下谁都救不了我。嗯,拧发条鸟,在我眼里世界整个是个空壳。我周围一切一切都像是骗子,不是骗子的只有我体内那片烂泥。”
这是最小剂量的“邪恶”酿成的灾祸,却能让人反观自己的种种邪念。或许能够容纳这一切的只有梦了,“拥有黑暗的心的人,只做黑暗的梦。更黑暗的心连梦都不做。”(《听风的歌》)
“他们将像剥桃子皮一样剥人皮”
在我看来,《奇鸟行状录》之于村上作品群的独特之处,就是从“间宫中尉的长话”这一节开始的。历史中的残酷事件,在小说中营造出比庸常的现实还要真实的质地,与“苦咖啡式”的、充满疏离感的主人公的生活产生了互动。这段“长话”中最惊人的,正是蒙古兵剥皮的描写。剥皮之前,俄国军官这样说:
“看好了么?好好看看这刀。这是剥皮专用刀,做得好极了,刀刃如剃刀一般薄一般锋利。他们的制作技术极其高超,毕竟剥动物皮剥了数千年之久。他们将像剥桃子皮一样剥人皮,熟练,漂亮,完美无缺。我讲得太快吗?”
军官前面的话是在恐吓藏有情报的山本,接下来的场面则一览无余地呈现给观看剥皮的间宫、听间宫讲述的冈田亨和读这本小说的读者……我无意引述血腥的场面,只想记录另一则令人不安的细节:
熊一般的外蒙军官最后把利利索索剥下的山本胴体的皮整张打开,那上面甚至连着乳头,那般惨不忍睹的东西那以前那以后我都没见过。一个人拿起来像晾床单一样晾在一边。
类似的细节见于《聊斋志异·画皮》:狞鬼将人皮铺在床上,用彩笔绘制,“已而掷笔,举皮,如振衣状,披于身”;等到道士杀鬼后卷那张人皮,“如卷画轴声”。作家贾行家评论道:“对敏感的读者来说,以后每次见到画轴,整个人都会有点儿不好了。细节重现,最能刺激情感记忆。”(《贾行家说<聊斋>》)
对剥皮的描写,我没有想起《红高粱家族》里日本人命令杀猪匠剥掉砍断他掳走的骡子腿的农民的皮的情节,倒是第一时间联想到莫言的另一本“幻觉现实主义”作品《檀香刑》里著名的凌迟:剥皮的“列锦”对应着五百刀凌迟,说起来还是后者更为恐怖残忍。小说家骆以军评论道,“莫言在此写到了一种行刑者、受刑者、围观者都被裹胁于一种琥珀般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、晕迷烂醉,既痛苦又甜蜜,既残虐又狂欢的奇幻催眠状态。这种‘技艺的疯狂痴迷’,有另一部关于传统技艺本身之极限妄念,不惜以人类肉身为其浮屠宝塔阶梯、剥夺、抽离、异化、‘去人类化’的魔鬼工匠技艺之典律,即聚斯金德《香水》。”(《无限阅读》)
刀子剥完中国人的皮,再去剥日本人的皮……此处重点应该不是传统价值观下的因果报应,而是皮对应的族群身份和刀子代表的糊涂战争。行刑之后,没有正义与光荣,剩下的是零散的血肉和恐惧。观众(读者)们如同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噩梦,然而那确实是历史。
24/06/30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