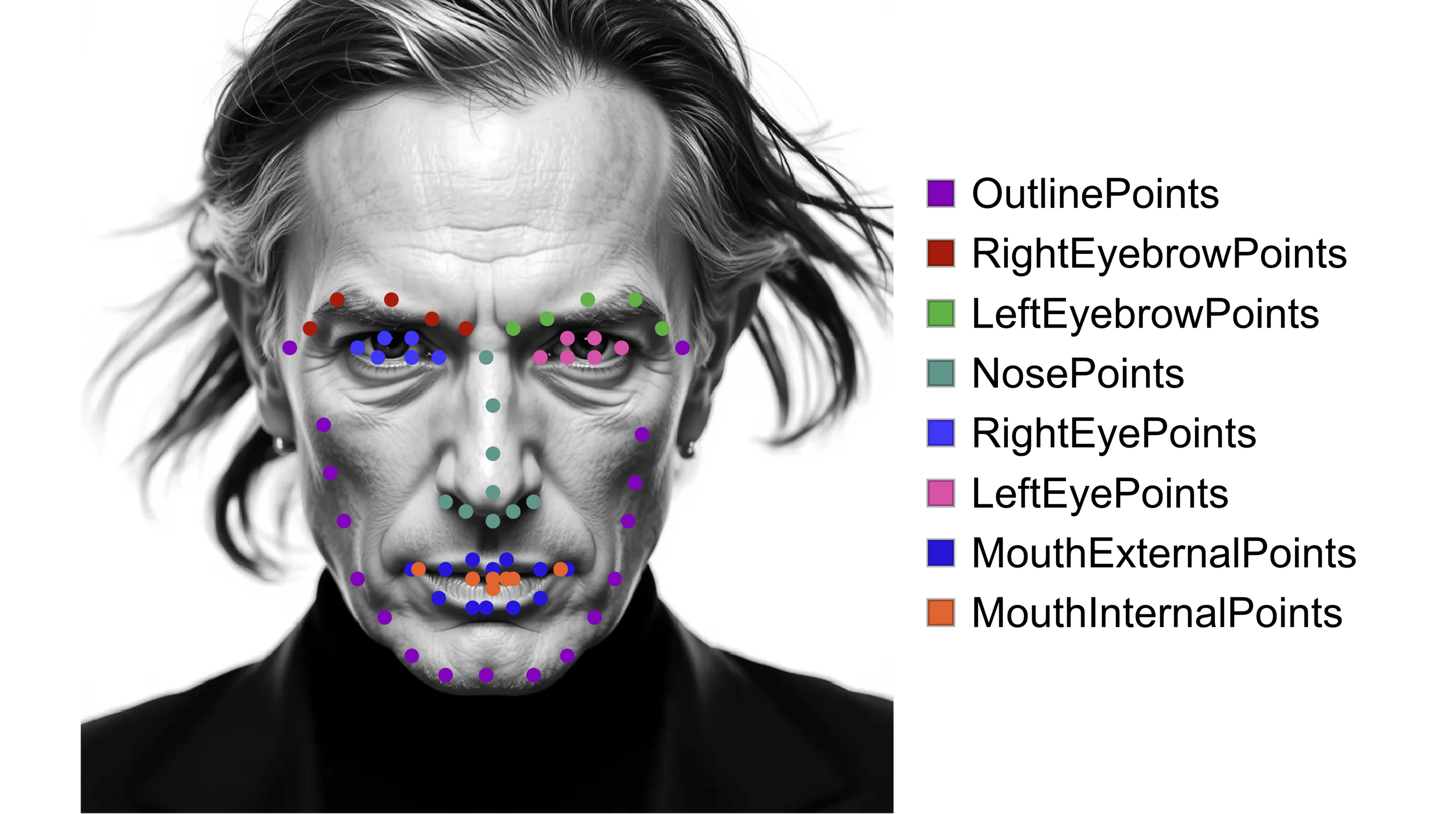
朱岳的小说集《脱缰之马》延续了自《睡觉大师》以来的荒诞风格,但这种荒诞演变得越发沉重,充斥着抑郁、乃至死亡的气息。
人脸识别
纳博科夫回忆录《说吧,记忆》中的一个细节,唤醒了我的儿时记忆:
我会理清漆布上迷宫般的回纹装饰,在一道裂纹或阴影为眼睛提供了一个 point de repère (参照点)时,我会找到一张张人脸。
《说吧,记忆》
同样,朱岳这本 2021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可谓“脸书”,多次出现“脸”的意象。比如,密集型的:
在《狮面》里,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圆柱体,向下不断投放狮子,“眼前狮子的数量迅速增加,形成一堵躁狂跃动的狮墙,一双双黄褐色的眼睛在雾障后瞪视着我。”
《圣路易斯》一篇中是类似的情景,这是一座曾经的动物园之城,在管理松懈之后,动物流窜于城市的每个角落,在结尾甚至出现了超现实的一幕:“动物的毛发已从密密麻麻、不可计数的细小孔洞中冒出,迅速覆盖了城市灰色的表面,尔后向着星空蔓延开去,房屋的窗口此刻已变形为幽幽闪烁的鳞片,也许在它们背面,一只或一万只眼睛正在睁大。人群惊慌地在街道上飞奔。”
《雅努斯》中出现了这样的细节,海面化作人脸拼成的百衲布:
我靠近大海,此时一个异象摄住了我。海上翻涌的波浪化作一张张人脸,整片海由面孔组成。无以计数的面孔平铺开去,无边无际,他们嘴唇翕动,像在讲着什么。但耳畔只有海风呜咽与背后传来的钟声。我跪下,把耳朵贴近冲向沙地的海浪,在面孔破碎前的一刻,捕捉到了泡沫般的只言片语。
《雅努斯》

首篇《六耳》中,“我”的左右肩头和左右手背长出新的耳朵,可以分别(幻)听到另外两句话,于是产生了话语和面孔不断增殖的恐怖细节:
推开窗,雾漫进来,凝望窗外,一片白色,我倏地产生一种幻觉:我的身上,包括六只耳朵上,冒出了无数小小的耳朵,淡粉色、密密麻麻,像一层疹子。与此同步,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众多面孔:亲人、老师、同学、同事、推销员、导游、路人……他们又将自身记忆深处的面孔召唤过来,挤到我面前,之后一齐开口向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,每一句话又被无数的耳朵转化为无数句话。
《六耳》
小说集中也出现了几次“脸的错认”的情节:
《约侬·列翰》中,转动画着“我”的面孔的魔方,面孔变得四分五裂。
《旅行史》中,“我”被算法错认为照片中在恒河边穿衣的印度男子,导游说,“不可能搞错,别小看现在的技术手段。还是想想怎么解释吧。”(延伸阅读:风格的幻觉与被存在的模特)逃跑过程中(后来发现是一场梦)发生了超现实的一幕,“我的面孔陡然往下滑移,连带着惊恐的眼睛一同掉落在地面上”,“原先面孔的位置像被一股强力抹了一下,一团模糊。”醒来后,“我”知道自己是登船“休眠”的人,真实世界中已是八十岁的身体和面孔。
我试图从知识库中搜索人类“识别人脸”的能力从何而来,没有很明确的结果。只有两条细节值得留意:其一是一则实验,研究发现受试者服用“左旋多巴”之后,识别人脸的能力得到提升,结论是多巴胺调节了人发现规律的能力(“识别人脸”的行为抽象成了“发现规律”的能力);其二是卡普格拉妄想症,患者会认为自己的亲人被某个相貌一样的人偷换了,作者认为人类在识别人脸时,不仅要看模样,还要依赖感觉。
我冒昧地猜想,小说里屡次出现的这种脸的“泛滥”与“错认”,与弥漫在全书中的癫狂与抑郁,是同源的。更为冒昧一些,我会认为这是情绪周期的体现。
幻觉迷宫
除《六耳》一篇外,《耳语》也在谈幻听,具体而言,是疲劳时产生耳语的幻觉。在这篇小说里,家住二十一楼的主人公,清晰听见楼下小花园里一位“狼人”的呓语。在主人公看来,幻听比幻视更难戳破,“ 我们看到某一影像,通过触摸的尝试,就可以验证其是真是幻,但幻听却难以判定。我们似乎是生存于声音的牢笼之中。”
“声音的牢笼”也是“话语的牢笼”。《传声》中设定了一个古怪的世界:两个人面对面如在交谈,口中传出的却是别人的声音,如果这两个人也要聊天,那就需要另外两个传声者的帮助。小说结尾,作者忍不住用“梦”来讽刺我们身处的世界:
我梦到自己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生活,在那里,只有不停说话才能存在下去,一旦闭口不语,就会消失,所以每个人都拼命说啊说啊,一刻也不敢停。
《传声》
《死亡之墙》这篇中的幻觉要暗黑得多,“我”像是被锁在一场梦里。小说开头,“我”因为好奇路边熟悉的班车开向哪里,就登上了这辆车。漫漫车程使我生出一种幻觉,“我的人生完全源于这辆车轻微的颠簸。”小说里写,“当我开始打盹,我们到了。”
这是说后面的一切都是梦境?
没人检查工作证,“我”就乘电梯到了建筑物的顶层,与一个陌生人交谈。他们谈起昨天有同事跳楼,他老婆的哭声“和今天的风声很像”。他们谈起跳楼的感受,陌生人说:“楼会显得很矮,像是只有四五层高。下面的东西都放大了。”“我”说:“就像一堵墙向你冲来。”
进入办公区,一位年轻女人早已认出“我”的陌生,交谈后,他们走上一条通往码头的走廊,看到被冲浪者称为“死亡之墙”的大浪。这一切像极了梦中对坠落的预演,“两只同样冰冷的手”,一堵向你冲来的墙。
《约侬·列翰》这篇基本对应于前作《李逵印象》,小说结尾提供了宿命般的死亡。奇怪的人递来一张卡片,请求签名,上面写着“(1940—1980)”。于是,“我”在那行字上面签了名。
他接过卡片,笑了笑,将手伸进怀中。我转过身,走向那块柔软的冰。枪声响起,我的身体被穿透,倒伏在极点上。枪又响了,但枪声似乎很遥远。
《约侬·列瀚》

方外之事
《跳》与《睡觉大师》(延伸阅读:朱岳的内在艺术)那一本里的《跑》相对应,从摆放位置来看,像是一篇后记。
小说(虽然更像散文)始于对“长跑型写作者”和“跳高型写作者”的讨论。“长跑”的要点不在快慢,而在坚持,这类写作者把写作融入生活,“他们无法过一种不写作的日子,这是他们坚持写到老、写到死前一两个星期的真实原因。”“跳高”的关键则是“最高的一次有多高”(肥尾效应?),如果心知不会跳得更高,就会主动退出,为读者节省时间,旁观者往往认为这叫“昙花一现”。
“我”的自我认同是后者,但实践中是前者,因为很难把握那个“最高点”所在何处(还是让人联想到投资),这就变成了另一种长跑,“身后留下心电图般的轨迹”。

接下来,小说的质地接近于现实主义。到结尾,一位道长在酒后给“我”算卦,没有看手相,也没有问生辰八字,直接说,“你做律师做不长,你做什么也做不成,唉,每条路都不通啊!”
接下去,道长没有提供收钱改命的服务,而是说,“你写小说吧,写小说这条路还通着。因为写小说是方外之事。”
这本小说集遍布着小说家的“忧虑”。
从《六耳》开篇,“我”让妻子念自己以前的小说,同时记录下“手耳”和“肩耳”所听到的内容,再从记录下的一百二十四篇里选出二十四篇结集出版。之后便是前面所提到的话语充塞的幻觉,似乎是对作品重复感的忧虑。《鉴赏家》一篇确实“重复”了前作《Aoz 盒子》的一个点子:把掌纹改编为小说。小说里会出现“这道伤口打断了我的叙事,血污浸没了应当交代的细节”之类的句子,还在飘忽的情节中塞了更多的点子,比如反复锤炼握手技巧的老板,以及无限延长两个音符之间空白的“极慢乐”。
在《想象》中,主治医师对“我”的“抑郁”进行诊断:
“你的病症源于过度运用想象力,为了写作,不断向大脑索取,就像在用一块海绵贪婪地吸食那点可怜的脑汁。你像对待奴隶一样压榨自己的大脑,大脑负担太重,导致了疲劳综合征。适度想象是一种享乐,过度想象是自我伤害。你看看,写小说的名家有几个身心健康的。
“我统计了一下,”他从白大褂的兜里取出一个小记事本,翻开读起来,“斯蒂文森活到四十四岁,中岛敦三十三岁去世,克莱斯特三十四岁,卡夫卡四十一岁,芥川龙之介三十五岁,莫泊桑不到四十三,爱伦·坡四十,奥威尔四十六,林燿德三十四,拉迪盖才二十岁就……”
《想象》
《潜水员》这篇里有无名写作者投水而死,将放手稿的背包丢进茅坑。后来,写作者的朋友把遗稿从粪水里勾出来。《死亡之墙》里年轻女人幻想中的丈夫用头脑封锁一场实际的海难,用山鲁佐德的方法延迟海难变成现实的进程,“他得不停地写,以各种方式、从各种角度写这件事”,“但终有一天,他会写不出来。”《心》的主人公会把一切伤害吞入心里,伤害他的人会从世上彻底消失,“仅仅一座小镇就让我的内心成了地狱。”
我联想到骆以军《匡超人》中的一段:
我们那么努力读着二十世纪的那些外国的伟大小说家的作品,其实只是努力学习怎样变成他们那样的疯子,那可是个比最深的矿坑坑道还深的地狱通道啊,我们逐字逐句,像是把旷野上的一座座疯人院,一砖一瓦地拆下,搬运到我们内心的某个地平线,在那依着我们记得的草图,重新盖起一座座疯人院。
《匡超人》
小说,实在是一种“内在艺术”,甚至是“内在忍术”。
24/09/24
